打“风钻”的经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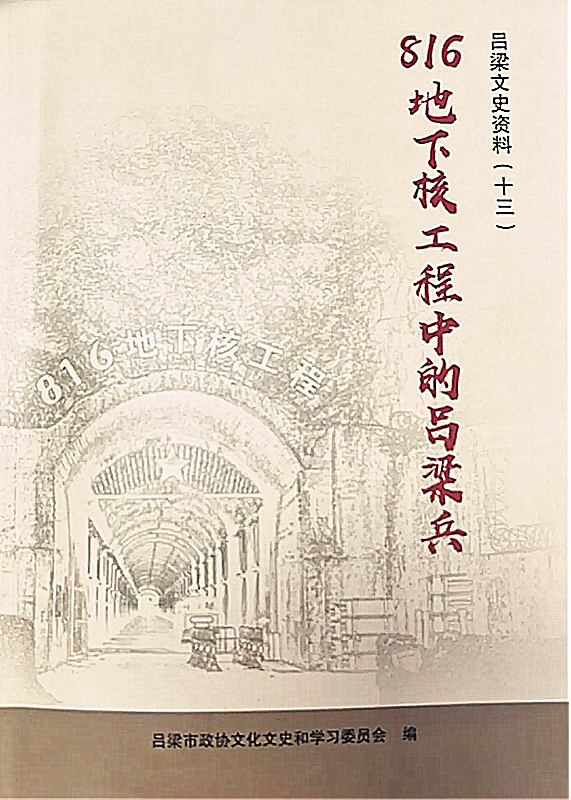
刘润保,1949年9月生,柳林西王家沟乡人,中共党员。1969年12月入伍,服役于8342部队101团2连,1975年退伍。
1969年冬,我搭最后一班车(年龄偏大),经严格政审(要求家庭出身必须是贫下中农),全面体检合格后,应征入伍到代号为8342特种兵部队当兵。由于保密,接兵人员根本不透露部队从事何种工作和任务,就连部队驻地都不告外界。接受了3个月新训后,仍一无所知,神秘感一直笼罩在我的心中。
当时被分到施工连队,亲眼目睹了部队的现实,思想上产生了“走当兵的路对了,进特种兵门错了”的波动。
说特种兵,其实叫石头兵更为准确,就是和石头打交道—打山洞。由于部队参与当地三支两军工作,工程进度缓慢,除主体洞室开挖之外,大部分还没开工。我所在的连队担负了6号洞的掘进任务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凿掘进、洞体打眼爆破,唯一的先进武器就是国外进口的风钻,风钻由钻机、钻杆、文架三部分组成,钻机上有进风孔、进水孔和升降开关,钻头由針杆和针头组合,支架主要是起到升降和钻杆平衡的支撑作用。钻重70斤左右,而且是由专人负责维护清洗保养。
新兵扛风钻往返保养房到坑道作业面,是不成文的潜规则。风钻操作手必须头戴安全帽,口戴如猪嘴似的防尘口罩,身穿防雨水的上下衣、脚穿高筒雨靴的全副武装。打炮眼很有讲究:必须按测绘员标好的红点进行,钻杆两面斜着先打掏巢孔,然后在左右两边和顶部打扩大孔,最后才是底部的翻渣孔,起到把炸下的石渣往前翻动的作用。
为减少粉尘和烟雾对人体的侵蚀,只能打水眼,不准打干眼,必须配戴防尘口罩,但因该口罩戴上给呼吸带来暂时的不舒畅,所以经常是形同虚设,成为摆设和样子,也为了日后矽肺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。打水眼时,由于风钻水孔密封不严,和钻杆上倒流回来的水一同顺着胳膊都流到了人的身上,夏季湿透全身,冬季既湿又冷。打干眼进度稍快点,所以经常是偷偷地打干眼。支撑架开关的操作也是很关键的,开大了突一下升上去,开小了很快会降下来,很容易造成钻杆断裂,钻头夹在炮限中。最危险的要数风管接头和风结结合部的螺丝松动,一旦脱落分离,风管犹如脱了缰的野马,容易伤到人。风钻操作还须风钻手和掌控钻杆两人密切配合,风钻手操作风钻的升降和注水,另一个人把控钻杆,不让钻头偏离位置。操作手掌握了要领,有时还可左右开弓同时操作两部风钻。
打风钻完成后,进人爆破阶段。炸药装填后,人员要疏散到安全地带,点炮顺序也是先掏巢,后扩大,最后翻渣孔。点火必须胆大、细心、快捷、灵敏,拿一根一米多长的导火线切开若干个口,先点燃后,再点燃二十几根装好的导火索。导火线点燃后发出嗖嗖的响声,让人很紧张、很恐惧。这项工作是由班排长和具有一定经验的老兵来完成的。爆破后的排险、扒渣交给下一班,就这样循环进行着。
装运爆破下来的石渣也是很艰苦的工作,尽管有临时铺设的轨道装渣机,但没有人工配合是进不了机斗的。小山似的石渣,要求短时间内清理完毕,力风钻手打钻创造条件。所以在铁锹上拴一根绳子,一个操控铁锹,两个拉绳子,把离装渣机较远的石渣扒到装渣机前(这就叫扒渣),劳动强度大,体力消耗大,扒渣几小时满手血泡,日复一日两手结了厚厚的老茧。助装渣机装进翻斗车后,由电瓶车运到坑口外,换小火车送到渣场存放和填沟。
风钻在坑口掘进和地下房间扩大成形上起到关键性作用,风钻操作手同样发挥了决定性的因素。
打风钻虽脏累苦,但锻炼了人的品质,磨炼了人的意志,培养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,激励我们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。
来源:《816地下核工程中的吕梁兵》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