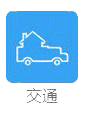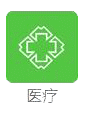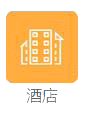咱们的结巴排长在哪里
1998年的10月中旬,我有幸回到了曾经在43年前生活、战斗过的第二故乡——山西省兴县张家塔村。多少年的夙愿实现了,当地的老年人们一再问我:“咱们的结巴(口吃)排长在哪里呢?”这、这,我该问谁去呢?结巴排长是我的顶头上司,也是我能够健康地活到现在的救命恩人。人民群众想念结巴排长,我何尝不想念呢。
在抗日战争时期,我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一二O师二十七团尖刀五连。我的排长,就是同当地人民打得火热的结巴排长。当时,我的年纪最小,个头最低。从整个部队来说,穿的、盖的、铺的、不说是一无所有吧,也实在是简单的太可怜了。那时我只有一块粗白布被子,没有任何可铺的东西,结巴排长就像我的哥哥一样,冬天睡觉时,总是让我睡在炕头上,晚上站岗,总要来回关照我几次。毛主席提出“生产自给,自力更生”的号召后,部队开展了种地、纺织、放牧等生产活动。在开荒地时,我使出吃奶的力气,还是远远拉到别人后头。结巴排长为了照顾我的体力,给我分配轻活,后来干脆让我上山放羊。因此,我就住在羊圈,冬天挨着大绵羊取暖,夏天和羊住在一起避免蚊子叮咬。那时候,我们生活比较艰苦,每日只供半斤黄豆的口粮(老秤八两),上午羊出坡的时候,我带一两重的四个窝窝头,挖点草根,吃点苦菜,这倒是又清火还充饥。晚上收坡回村,觉的肚里边还是饱饱的,节省下两个窝窝头给结巴排长。可结巴排长舍不得吃,他又将两个窝窝头给了排里几个力气大、个头高的战士充饥。

在打仗时,他总是冲锋在前,退却在后。我记得1945年中秋节的这天,我军于拂晓攻入绥远省(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)的归绥城(今呼和浩特市)。我们这个排爬到了老乡们的房顶上,与日伪军对峙,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我的结巴排长和我并肩战斗,事事处处关照着我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,归绥城的房子又大部分是土坯房,一下雨爬都爬不住,我和排长只能互相紧靠,才能保护自己消灭敌人。此时,我们有一位班长站起来向敌人喊口号,让他们放下武器交械投降。一句话未完,敌人就开了枪,英雄的班长当场壮烈牺牲了。此情此景激起我报仇的怒火,我没顾得考虑自己的安危,站起身来随手向敌人投去手榴弹。这下结巴排长火冒三丈着急了,边拖我边喊:“姚…文…锦…不要命了。”顺手一把将我拖倒。眨眼之间,敌人扫来一排子弹。多险哪!没有结巴排长拖我一把,这一次我就牺牲了。
1945年11月8日,在八里庄战斗中,我和结巴排长同天负伤,因伤员太多,转送也较困难,开头我乘牛车,因道路不平,震动太大,我昏迷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,在什么时候苏醒也不知道,身上穿的一件破棉衣也被人脱走了,只留下一条破棉裤。我这次除受到贯穿性枪伤外,两只脚都被冻坏。大概过了三四天时间,幸好我原来的副连长陈继祖同志这时在团部任副官,他在收容工作中,发现我在一辆牛车上呻吟,设法搞到担架,就用门板将我转移到丰镇县的一个农村。这时医院的同志履行登记手续,当询问我是否共产党员时,我的党证缝在棉衣内,棉衣被人剥走,其它物品也全部丢失。正在为难之际,我的结巴排长正好转移到这个地方。他在担架上就听到了我的声音,他当即证明我是共产党员。从此,我又和结巴排长住在一个村了。
我住医院不到10天时间,两只脚全部腐烂。医院决定给我截去双脚。这时,我自己做不了主,要医生请示我的排长,他果断的地回答,不同意锯掉我的脚。就这样,我的两只脚完完全全地保留下来了。现在50多年过去了,我的双脚虽然留有残疾,但行动走路全不碍事。
后来我在部队做领导工作,每当行军作战和训练,和我的排长一样,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。现在,不仅两脚全在,只不过多次负伤致成二等甲级残废,伤口变形时有疼痛。但我日常生活过得非常幸福。遗憾的是我的恩人结巴排长不知到了哪里,这已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
我的排长在战斗中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;在克服生产、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时,是心灵手巧的多面手;在行军和宿营时,他每到一处都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张家塔村人民群众一再询问:“咱们的结巴排长在哪里?”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。我和大家一样,也很想知道我的恩人,我的排长您现在在那里?1946年元月,因敌人捣乱,我俩在丰镇分手后,直到今日无任何联系。当时我俩的团长是兴中同志,营长是刘籍甫同志,连长是李汇海同志。以上各位首长知道尖刀五连二排长的情况吗?或者新闻媒介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吗?
敬请各方面帮忙,切盼。(作者系兴县姚家会人,太原离休干部。)
作者:姚文锦
来源:《吕梁回忆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