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红色记忆】参与816工程点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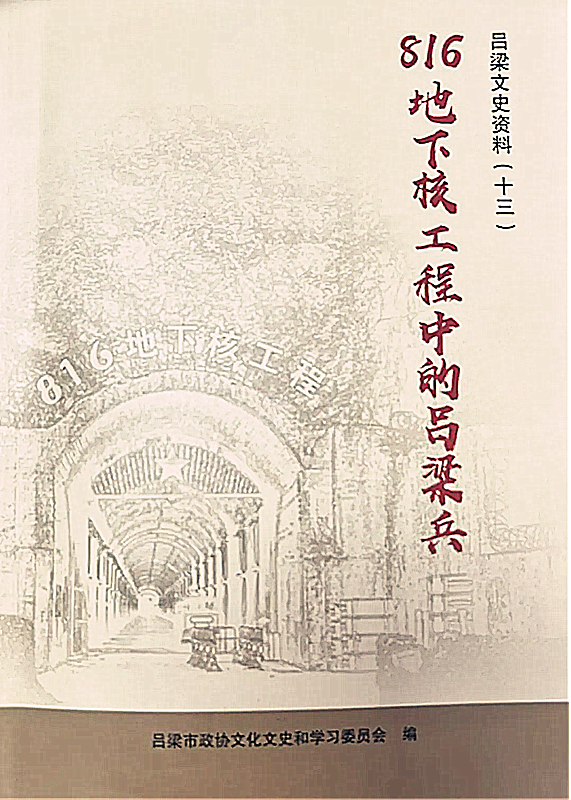
1969年底,我和来自离石的30名战友被分配到工程兵建筑54师101 团14连。
入伍第一年,我们14 连驻扎在甘肃省敦煌县,在海拔4000多米高的阿尔金山开采石棉。在荒无人烟、高山缺氧、地势险峻、气候恶劣的条件下,战士们靠镐刨肩背,全年开采石棉300多吨,收入近10万元。我作为连队给养员,起早睡晚,风餐露宿,竭尽全力保证了连队物资和副食品的供应。
1970年冬,连队回归四川大部队,投人到816核工程建设中。1971年初,我担任副排长。当时排里没有排长。一个离开校门不久、入伍只有一年的新兵,要带好资历都比自己老的8个班长、副班长和全排40多名战士,困难可想而知。我坚持向别人学习,从自身做起,顺利闯过了第一关。
我们连担负全团公差勤务的工作,干得最多的是装卸水泥,除了超负荷的体力消耗外,还要遭受粉尘的危害。遇到装卸散水泥,扬起的灰尘呛得睁不开眼,撒得浑身上下都是,防尘口罩根本无济于事,鼻孔里的水泥结成块,吐口唾沫里边都是水泥。天气淡热,工作量大,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,水泥沾在脸上、身上,满险乌黑,只留下个白服珠,大家你瞅瞅我,我瞅瞅你,居然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
记得有一次,码头上运来一百多吨水泥必须马上卸船。正午时分,骄阳似火,我们全排的同志豁出命来干。一袋水泥100斤重,有不少人一次扛两袋。干了两三个小时后,就有五六个人暴国在地,连平时力气最大的同志也都吃不消了,但大家前仆后继,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。
那一年,816主体工程掘进到了关键时期,团里的口号是“苦干实干拼命干,全年拿下十五万(立方)。”年初开门红、迎战红五月、时间过半任务过半,向党的生目、建军节、国庆节献礼,年底大会战,施工热潮一浪高过一浪。
我们排担负洞室扒渣的任务,在施工机械无法作业的地带人工清理渣石。洞内阴暗潮湿,空气混独,硝烟弥漫,环境极其恶劣。风钻声、机械声、爆炸声,声声震耳欲聋;粉尘、烟尘、矽尘,尘尘侵肺入腹;大塌方排哑炮司空见怪,小冒顶炸伤人家常便饭。作业面险象环生,随时有塌方的危险。战士们用铁锹、十字镐把爆破炸出来的石块、石渣清理到可以使用铲车的地方,对原先爆破不彻底的地方进行二次爆破。有一次全排先后有20多名战士晕倒在作业面上,被迫撤出洞外,躺在石堆上喘息。连部卫生员提着水壶,拿几袋“仁丹”,每人服一点“仁丹”,喝上两口水,然后再进洞继续干。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,始终不肯向困难低头。
816 部队驻扎在素有中国四大“火炉”之称的重庆地区,夏天天气炎热,秋冬阴雨连绵,各种疾病丛生。夏天,军营爆发了传染性痢疾,多数人被感染,发病人数过半,有的战士一天要跑几十趟厕所,便干脆拉一块草席躺在厕所旁边。防治措施跟不上,战士只能靠节食、喝白开水硬撑。秋天,由于气候潮湿,又开始流行烂裆病。瘙痒、糜烂、渗血,药物效果甚微,边治边患,苦不堪言,战士们只能默默忍受,带病上班。
当时我们还搞了一次献血。那天,我们营11 连有4名战士受重伤,急需大量血浆。正好我们排当天没有公差,在营房学习待命,就被派去献血,每人献三四百毫升。我是◎型血,又是带队的领导,自然一马当先,战士们也都争先恐后,金排有十几名战士献了血。
816 工程施工过程中,爆破、冒顶、落石、车辆机械损伤以及其他各种意外事故时有发生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排奉命到一碗水去安葬烈士。时逢冬天,外面一片漆黑,又下着雨,当时的坟地还是个乱石岗子,十字镐刨不下去,只得用炸药炸。一碗水烈士陵园里有几十座坟墓,看着那一座座年轻战友们的坟墓,大伙儿心里都感到沉甸甸的。
参加816核工程建设,是我12年军旅生涯中最有意义、最值得怀念的岁月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经受了考验,也得到了成长。我们为祖国奉献了青春,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我们。我们离石县的30名战友中,多数人入了觉,有的被提拔为班、排长,我和白凤明、郭光亮等同志还菜立了三等功。我们续写了和平年代“吕梁英雄传”的新篇章,为昌梁人民争了光。
1978年,我被调到长沙工程反学校担任地雷、爆破教员。
1981年底转业回乡。2009年退休。
来源:《816地下核工程中的吕梁兵》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