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红色记忆】特种工程测绘二三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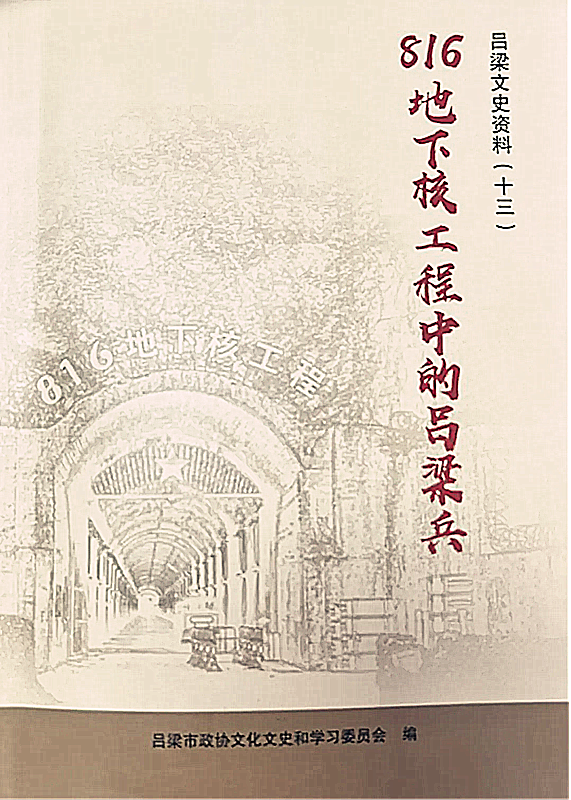
特种兵的诱惑
我家在柳林县金家庄乡,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。那个年代,高中毕业生算文化人,可我没门路找不到工作,连村里的民办教师都轮不上。高考无望,工作渺茫,正当我在人生起点徘徊时,接兵部队来到了村里。1969 年冬季的一天,广播里播放了征兵消息 —— 对当时因各种原因迷茫的我来说,无疑是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和接兵班长接触后,我得知这次征的是特种兵,政审严格,必须是贫下中农。追问去部队干什么,对方回答 “扛大石头”,语气看似肯定,可谁会相信干苦力活需要如此苛刻的政审?那时,我双亲年迈需要侍奉,自己又是大龄青年,家人都盼着我早日成家。但我完全符合应征条件,当特种兵更是难得的机遇 —— 既能离开家看看外面的世界,又能享受 “当兵光荣” 的荣誉,生活条件也有保障。于是我决定报名,政审、体检一路顺利,穿上不太合身的新军装,走进了解放军特种工程兵 54 师的军营。
测绘兵的天职
3 个月的新兵训练又苦又累还紧张,但我觉得一切新鲜,自我感觉良好。新兵中我年龄最大,却总守在队尾(任 16 班副),心里有些不自在。好在短暂的三个月很快结束,我被分到 101 团 3 营 13 连 16 班。第二天上午,指导员找我谈话:“你的文化程度高,理解能力强,把你调到营部测绘班,已经有人来接了。” 当时我对测绘不甚了解,有点消极情绪,但还是服从安排去了。
测绘班长是 1968 年入伍的安徽兵,技术员叫许沛,上海人,是个幽默风趣又要求严格的知识分子。欢迎会上,许技术员一字一句庄重地讲解测绘员的职责:测绘工作既重要又辛苦,是连队施工的 “导航仪”,必须具备高度责任心和精准技术,要一丝不苟地制定施工方案,指导施工方位、方向及打眼深度、孔距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“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部队损失、影响工程质量,会按事故论处。” 那次班会至今记忆犹新,既给了我一个 “下马威”,也让 “一丝不苟” 成为我 4 年服役期乃至一生的训令。
工地值班的艰辛
我高中课程只学了三分之一,却已是新兵中少有的 “知识分子”。虽没经过专门培训,但在老兵传帮带下,加上自己刻苦钻研,很快掌握了测量仪使用、识图计算等知识,开始驻工地值班、独立工作。从营房到工地约一公里,要步行下山、过沟、上坡,沿途全是石砌台阶,得走半小时。为更好服务一线,部队决定 “指挥前移”,在工地建了值班室,由一位营首长、一名通讯员、两名测绘员常住。值班室的设施、衣食住行都更简陋,没有运动场所,生活单调又寂寞。记得有天夜里,一条大花蛇钻进值班室,吓了我一跳。
连队不配备测绘员,营测绘班自然成了冲锋在第一线的战斗员。除平时依据图纸测量定方位、标高,我们还要 24 小时随连队换班 —— 每个班次必须在风钻手到位前,根据爆破后的作业面情况,为下一班施工完成标高、炮眼位置的画线任务。为不影响连队抢进度,我们常在炮后烟雾未散、排险未完时,就扛着测绘仪、提着油漆桶进洞画线。防尘口罩要换滤纸滤布,一个班下来,口罩已一片黑灰。
坑道里常常险象环生。有一次,我从值班室下到二号坑道时,接班人员还没到,放炮后的烟雾浓得伸手不见五指,炸药味呛得人呼吸困难。走到作业面,手电光被烟雾笼罩得模糊不清,我正蹲下提漆筒,突然一声巨响,天旋地转,顶板的石子如暴雨般落下,我连人带漆筒被掀倒,滚下渣堆,差点丢了性命。后来才知道,是未排除的哑炮引发了爆炸。幸好戴着安全帽,没被砸伤,但耳朵震得轰鸣、眼泪直流,过了两周才逐渐恢复。那次教训深刻:测绘员不能心急,必须遵守规程,排险后再进现场,否则可能丧命。
感恩的心
如今,我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兵,回望人生轨迹,真该向特种工程兵 54 师部队致以赤诚的感恩。是部队把我从迷茫中引上光明大道,避免了人生可能的曲折;是部队这个大熔炉,把我从懵懂青年培养成共产党员,让我具备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,为确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打下基础;也让我学到一技之长,为回到地方求职创造了条件。
(作者:刘发斗 来源:《816 地下核工程中的吕梁兵》)
















